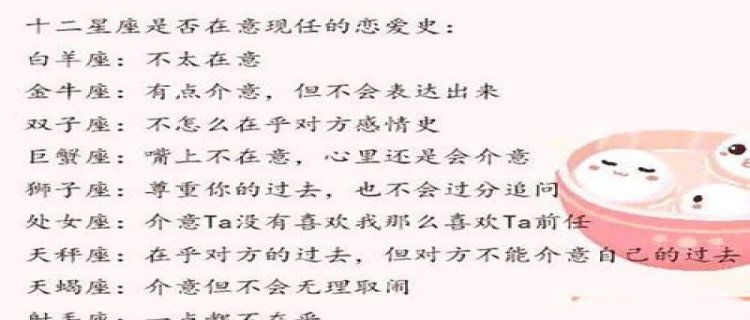老同学:干这行,不怕被雷劈?
李建军:混口饭吃。
老同学:混饭吃的方式有很多,为什么要在医院当黄牛?
李建军:因为火车票已经没什么市场了。
老同学:我是问为什么一定要当黄牛?
李建军:混口饭吃。
老同学:劝你还是找个正经工作。
李建军:找我什么事?
老同学:那个…有没有风湿科的号?
李建军:有,4500元.
老同学:老同学你也宰,能不能讲点感情?
李建军:如果感情是用来讨价还价的,那感情也不值钱。
李建军是个黄牛,倒卖医院的号。
很多人咒骂这个职业,然而急需之时,还是会找黄牛。
只要你要,李建军什么号都能给你弄到。
他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很缺德,
但他又觉得,
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,他不做黄牛,别人会做。
如果上天一定需要几个缺德的人,他愿意自告奋勇。
咒骂黄牛的人认为,如果没有黄牛,挂号机会人人平等。
有了黄牛,名医专家号大多被有钱人买走,这样对穷人公平吗?
不公平。
但在这个城市,
房价很高,公平吗?
换个心脏很贵,公平吗?
买得起学区房的家庭的子女能读最好的学校,公平吗?
可以说不公平,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竭尽全力都够不着,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拥有。
别再说什么输在起跑线上,我们连上跑道的资格都没有。
但也可以说公平,因为商品就在那里,谁支付,谁拥有。
李建军做黄牛的目的很简单,多攒点钱,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过得好一点,
过得有多好?以后就算看病,花4500买号也不会心疼的那种好。
大家赚钱的目的都是一样,只是每个人的手法不同,
手法虽有不堪,但胜过没钱的窘迫。
这是李建军的想法。
也是很多人的想法。
这一天,李建军,游荡在医院大堂,察言观色,寻找目标客户。
李建军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,他能一眼看出来谁需要号。
他有很多号,每一个都值至少4500。
他观察一个农妇很久,他认为她就是目标客户。
这个农妇牵着一个五岁多的孩子,显得有些无助。
李建军走过去,经过一番交谈,报了个价。
农妇从棉袄里掏出一个布袋钱包,把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,数了数,三百二十块五角。
农妇看了看李建军,眼神里更加无助。
李建军摇摇头,离开。
他觉得农妇浪费了他的时间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李建军开始变得冷漠,他甚至有点歧视穷人,虽然他自己也不是富人。
社会存在着一条歧视链,这个链是封闭的,每个人都歧视着不如自己的人,也被比自己牛逼的人歧视着。
食物链维持着生态平衡,歧视链维持着社会平衡。
这个城市从来不缺乏温暖人心的爱心新闻,
但更多的是冷漠,
谁经历,谁知道。
李建军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,继续察言观色,寻找目标客户。
他环顾一周,没发现合适的客户,却看到刚才那个农妇蹲在墙角,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和一个餐盒。
餐盒里面黑乎乎的,似乎是雪菜肉丝。
农妇咬了一口馒头,用筷子把雪菜肉丝里的肉丝挑了出来,填进馒头月牙形的缺口,递给小孩。
小孩接过去,狼吞虎咽。
李建军看到这一幕,想起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:
穷人孩子的母亲,是把肉挑出来给孩子吃。
而富人孩子的母亲,都希望孩子多吃点蔬菜。
这一幕太熟悉,让李建军想起自己小时候。
他看到农妇,想起了自己的母亲,
他看到小孩,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
李建军叹了口气,走过去,把号免费送给了那个农妇,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
李建军想起母亲去世前的一句话:好好做人。
这一刻,他做了个决定。
他拿出电话打给他的黄牛老板:“我不干了。”
他离开医院。
他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,却无法面对一个把肉丝挑出来给小孩吃的母亲。
他不想赚这种钱了。
他想回老家过年,春节后重新找个正经工作。
李建军走出医院后,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。
他去餐厅要了两份炒菜,一份米饭,一份馒头。
打包,热乎乎的。
他拎着饭菜走进医院,寻找那对母子。
这一刻,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得到了新生。
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
但他却看到了农妇把号塞给了另外一个人,那个人给农妇塞了一大把钱。
农妇的眼神,跟刚才完全不同。
李建军知道,那是黄牛的眼神。
他被同行坑了。
他善于察言观色,但她更善于表演。
李建军把饭菜丢进垃圾箱,拨通老板的电话:“刚才开玩笑的,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