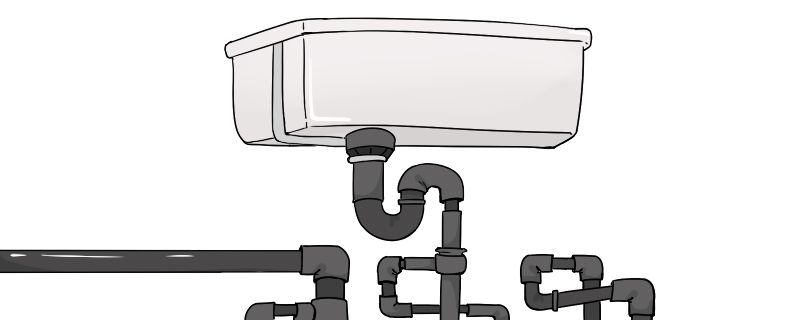去过草场地的人都说,那里是个独立的小王国。它气质独特,以至于初到这里的人总会惊讶:北京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。
过去的一周,我在这个充满现实魔幻主义的地方待了两天一夜。
离草场地还有1000米的时候,我被堵在了机场辅路上。对于这里的堵车,司机师傅已经习惯了,他告诉我,堵上一个小时都正常,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,只能慢慢挪。
为了早点进入草场地,我选择了下车。
但下一刻我就后悔了。跟着导航我走到一条长满荒草的路上,再往里走,还是不见人烟,直到靠近一座灰色砖瓦的院子,我才看到一位蹲在地上刷牙的女士。她告诉我,这里只是草场村的村边,加之是早上,所以瞧不见什么人,
最终,跟着一位村民模样的人,穿过没有红绿灯的马路,再爬上台阶我才到达目的地。
第一眼我就知道,这就是我要找的草场地村。
早上8点多,正是上班时间,不断有年轻人从村子里匆匆走出,他们穿着通勤服装走在灰色的水泥地上,还要留意路边遗留的垃圾。村口有家旧货市场,隔不远处就是开在川菜馆里的早点铺。
我在其中一个桌子上搞定了早餐:一碗粥,一个鸡蛋,3.5块。而我旁边的桌子在10分钟内换了3波人,他们多是两人作伴,点一笼小笼包加两碗粥。老板身后的桌上放着几碟咸菜,想吃可以自取。每张简易桌下都随意躺着一次性筷子的包装膜、揉成一团的餐巾纸,在苍蝇飞绕、满是油渍的地面,这些遗留物并不违和。

满头大汗的老板娘一边取着小笼包,一边扯着嗓子喊:你是要一笼肉包子加两根油条吗?
这样的早餐铺在草场村还有很多家。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小吃店,站在十字路口往村里看,林立的小饭馆招牌和上空乱拉的电线就是这里的基调。再往里走,你还会依次经过烤串店、烧饼铺、水果摊以及便利店。

不过,在早上,除了早点摊之外的店铺是无法挽留步履匆匆的上班族的。
当这些外来客潮水般涌出村子,草场地就迎来了属于村民自己的时光。
一户人家把桌子搬到门口开始吃两菜一汤;一位阿婆背着孙子慢悠悠走在不太干净的路面;守着水果摊的年轻人在低头玩游戏;晚起的刘老头光着膀子站在自家门口,左右张望;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从胡同里冒出来,捧着一碗面糊糊小心翼翼走向正在看店的父亲。
而拾荒老人们,已经把村口和路边的大小垃圾桶翻了个遍。
工作日的白天,新来找房的人总是最扎眼的。他们眼睛里充满好奇,偶尔也有困惑,犹疑徘徊在一栋栋村民自建房前,看到“有房出租”的广告,就开始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

还有人是直接拖着行李箱来找房的。这里的房租可以按月结,只要有合适房源,当场敲定就能入住。
到晚上,草场地就换上了另一张脸。
草场地的日与夜是割裂的。
晚上6点以后,林立错乱的小招牌渐渐亮了起来,草场地开始属于年轻人。白天门庭冷清的馆子完全变了样,年轻人三三两两围着心仪的摊位或馆子,聊着白天的日常,抑或拎着刀削面、炸酱面、盖饭,悠然走向回家的路上。

串吧总是热闹的。新疆馆子烤羊肉串时风扇的呼呼声,也挡不住喝酒人的吆喝声。有下班早又减肥的女孩,索性绕开饭馆,去为数不多的那几家服装店里逛一逛。
于是,空气里的味道也开始变得复杂。烧烤味、臭豆腐味、煮玉米味甚至是糊锅味都混杂在草场地错综复杂的小街里。

在夏天,这样的热闹会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多。灯光阑珊中,草场地的满身膏药几乎隐匿不见,它们包括满墙的小广告,随处可见的乌黑垃圾桶,以及宠物狗们的随意大小便。
相比北京城的迅猛变化,草场地像个被遗忘的孩子。
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初,当时这里是皇家御马苑的草料场和牧马之地,得名“草厂地” ,解放后统一制作村名标牌变为“草场地”,沿用至今。
如今,草场地与草厂地在这里并存——后者是艺术区,2002年之后陆续建,似乎为了与草场地村区分开来,村口同时挂着两块村牌:草场地、草厂地国际艺术村。

外人很难清晰区分两者。通常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,有些地方完全融合在一起,即便你在地图上输入不同的两个名字,得到的地点也是重合在一起的。
但在村里多走上几圈,你就能感受到这里有两个世界。
环绕草场地村而建的艺术区,被统一设计成灰色砖墙的样子,出入其中的不是艺术从业者就是外国人。随意经过一个院门,你就能听到里面有人在讨论,某人的画风太油腻。
他们喜欢草场地的低廉房租,也喜欢艺术与粗糙城中村生活相遇的冲击感——前一秒,你可能还在油渍满地苍蝇乱飞的川菜馆里吃着包子,下一秒可能就坐在复古咖啡店里,慵懒地倚在天鹅绒沙发上,在柔和的音乐中跟朋友畅谈。

画漆画的林程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切换中。
她两年前来到这里,如今拥有一家工作室。粉白墙面,青色屋檐,从窗户望进去,能看到一盏来自宜家的雕花吊灯。入夜后,灯光让整个房间显得柔和起来。窗外,还有一大丛正在盛开的紫茉莉。
这样的恬静和整个村子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。

她不在乎。我赶到的时候,她正在调制树漆。谈及为何选择草场地,她答:房租便宜,周围还有一些艺术家画廊,氛围还算可以。
林程所在圈子的艺术家们,大多瞧不上一公里开外的798艺术区。那里已经变成游客的地盘。
在林程看来,草场村所有的脏乱差只是城乡冲击的自然状态,“毕竟都建成CBD,也挺没意思的。
草场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它与艺术区的割裂明显而又模糊。
在这里,艺术展览区和肉夹馍小店的距离只是一个拐角。在同一栋建筑里,你可以在一面看到梵高的星夜图,在另一面看到洗衣房入口。小路两侧,一边是赤裸上身暴露啤酒肚的村民,一边则是说着其他语言抽烟聊天的外国人。

林程喜欢这种混搭的感觉,很多艺术的灵感往往是从凌乱和反差中迸发而出的。
他曾经在某艺术家工作室外看到一只眼神纯净,连脚趾都干净的小土狗,它从容地走在青砖路上,一点也不怕人,而几百米外,草场地的大街上,一只原本雪白的雪纳瑞,耳朵被染成粉红色、四肢也沾满泥渍。
“从出身来看,这两只狗的狗生应该对换的,却在几百米内上演了反转命运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刺激的吗?”
如果说冲击感是艺术家对草场地的感受,人情味则是租客对这里的关键词。
河北姑娘李梦住在这里3年了,在她看来草场村什么都好:吃饭购物都方便,楼下就是超市。
李梦喜欢人气足的地方。来草场地之前,李梦通过在自如租了一年房了,房客相互之间都不认识,有时快递都没人代签。
而来这里的第二天,李梦就认识了楼上的小蕾。当时她正在楼顶晾衣服,小蕾笑着问:你是刚搬过来的吗?
就这样两人认识了。下班后,她们经常相约在楼下买酱香饼和水果,如果不累,还会跑去望京看电影和吃饭。
离望京不远,这也是李梦喜欢草场地的理由之一。从这里开车到望京只需要十几分钟,走在村里抬头就能看到望京SOHO。李梦还知道一条小路,走路半小时就能到公司。

比起以前在天通苑租房的时候,李梦觉得此时很幸福,至少不用挤地铁了。
但这里的公共交通并不方便:远离地铁口,仅有的三趟公交也是指望不上的。每天早上8点以后,共享单车也基本都被骑走了。
最理想的出行方式是电动车。很多望京的房产中介都住在这里,每天早晚,这支穿着西装骑电动车的大军,就会成为出入草场地的独特景观。
李梦有时候也会搭男同事的电动车上下班。在草场地,另一种人情味来自房东。
住在草场地三年,李梦跟房东已经成了朋友。刚来时,她总爱大声说话,住在楼上的房东有时候会跑下来,提醒她小声一点。这总她恍惚觉得又回到了大学时光——只是楼管变成了房东。
相比楼管,房东的照顾似乎更多一点。有时房东家饭做多了,会给李梦留上一碗,赶上刮风下雨天,房东也会帮忙收晾在天台的衣服。
草场地的房东大多是村民。每家的自建房格局类似,四层或者五层高,根据面积大小隔出一个个独立房间,房东跟租客一起住在楼里。

李梦记得,两年前村里的出租房还大多不带独立卫浴,但随着年轻人对居住条件要求越来越高,房东也开始顺势而为,重新搞装修增加卫生间,当然,房租也随之从800元左右涨到了1400元左右。
草场地里住的人很杂。
李梦住的那层楼,既有一家三口,也有小情侣和单身人士。既有做建筑的,也有搞金融的,有一段时间还住进了一个会说汉语的外国人。
但李梦没有因此而觉得不安全。她性子有些大大咧咧,好几次出门都忘记上锁,也没出过什么事。在北京城,这样的夜不闭户多少有点理想国的味道。
草场地的租客们,大多就在附近工作,更精准一点的说法是:在望京工作。
白天,他们是吹着空调出入锃亮大理石厕所的白领,抑或谈着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生意的房产中介,晚上,他们回到草场地,买上一份5块钱的烤冷面,进入下班后的休闲时光。
白天抽着精致烟踩着高跟、流利说着外语的女生,在村里的房间里说起了方言,向父母汇报自己一切都好。
人们在草场地割裂着日与夜的自己,而草场地包容下了一切。
这里物价低廉房租友好。走在村里,你很容易看到穿着暴露的少女,手牵手的拉拉,以及纹着花臂的男人。无论是外国人,还是艺术家,北漂,大家都相互不干涉,谁都见怪不怪。

总有一批批年轻人通过朋友,或者朋友的朋友介绍来到这里,住到不再需要仰望望京的时候就离开。
就这样,来来去去的年轻人成了村里流动的风景。
这里的年轻人也爱玩王者荣耀,爱淘宝,爱点外卖,他们唯独不太关心的是房价——或者,是假装不关心。
李梦公司附近的小区,均价已经超过10万,她算过,10万块相当于她一年的工资,这笔钱能在望京买到一平米的10万块,能在草场地租7年房。
但这个算法里隐藏着诸多变量。
今年以来,附近东辛店村拆迁,大量租住在那里的民工流入草场地,李梦的房东已经通知准备涨房租了。更长远看来,无人能肯定,这片紧靠五环的城中村,会不会也在拆迁中消失?
世事变迁。不过,对于在草场地生活过的多数年轻人来说,当他们开始融入北京城,开始在郊区甚至更远的燕郊买房置业,开始研究带孩子上哪个课外班,开始帮助孩子填报中考志愿,这片村庄,以及村里的时光,总归会是记忆里鲜活年轻有生机的那部分。
那是属于廉价、青春和荒蛮的独立王国。